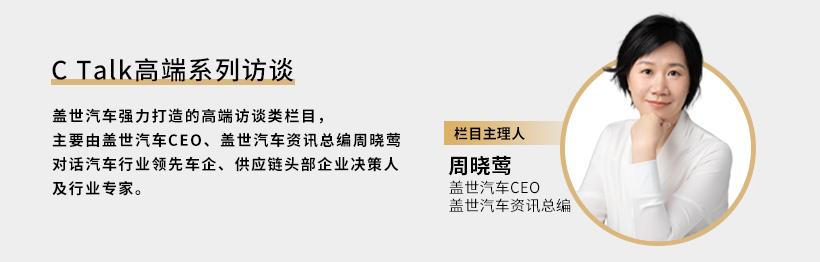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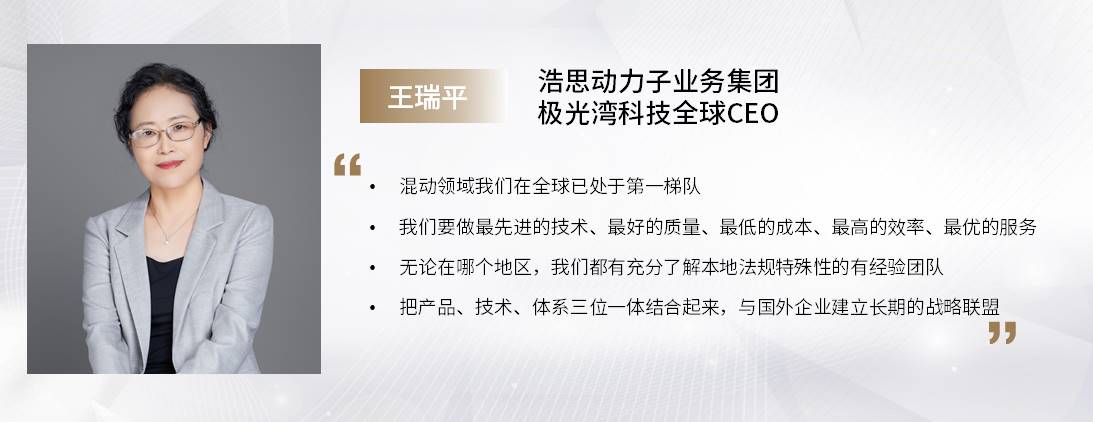
对话 | C Talk栏目主理人、盖世汽车CEO兼资讯总编 周晓莺
撰文 | 盖世汽车编辑 苗雨竹
全球汽车产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权力重构。
当电气化、智能化浪潮席卷而至,传统汽车市场上,原本以欧、美、日等为主导的行业技术壁垒正在逐步瓦解,一条以中国市场为策源地、以新能源技术为突破口、以“技术+体系”双输出为特征的全球化新路径,正在重新书写世界汽车的竞争规则。
在这场静默却剧烈的变革中,中国汽车产业链的出海模式,也已经悄然生变,已经开始从过去“以价取胜”的单一产品贸易,升级为“以技术赋能”为主的生态共建,而这,也正是浩思动力子业务集团-极光湾科技全球CEO王瑞平,在全球顶级舞台2025 IAA Mobility上,与盖世汽车交流时所展现出的战略底气。
“我们不是简单地卖产品,而是把产品、技术加体系三位一体结合起来,与国外企业建立长期的战略联盟。”王瑞平语气坚定地表态,不仅概括了浩思动力出海的核心理念,也折射出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舞台上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变——从产品输出迈向技术输出,从单打独斗转向生态共建。
浩思动力是吉利和雷诺共同成立的全球动力科技公司,承载着双方在高效动力系统和混合动力领域的技术积淀和国际化野心。“我们在全球已经处于第一梯队,”王瑞平在谈到中国混合动力技术时如是说。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汽车工业过去六、七年间,在新能源转型浪潮中不断积累、迭代、突破的缩影。从早期的技术引进,到如今的自主创新甚至反向输出,中国动力总成企业正在改写全球汽车技术竞争的新格局。
在2025 IAA的展馆中,中国企业与欧洲企业几乎“平分秋色”的参展阵容,也印证了王瑞平的判断:中国汽车产业已从昔日的学习者、追随者,成长为今天的参与者、甚至是引领者。而浩思动力,正是这一进程中的代表之一——不仅输出产品,更输出技术、标准与合作模式。
“我们要做就做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质量、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最优的服务。”王瑞平这句掷地有声的口号,不仅是对浩思动力自身定位的总结,也是对中国汽车产业链整体能力的自信宣言。王瑞平认为中国企业的出海之路,本质上是一场“从青春期走向成熟”的必然过程——不再局限于本土市场,而是要在更广阔的全球舞台上,与顶尖玩家同台竞技,共建生态。
当然,全面出海的“战役”肯定也不会一帆风顺。王瑞平也坦言,不同市场的法规差异、文化融合、供应链本土化等问题,都是出海路上必须面对的“硬骨头”。尤其是在欧美这类对安全、排放等有极高要求的市场,如何将中国“快”的研发节奏与当地“稳”的验证体系相结合,是考验企业全球化能力的关键。
“无论在哪个地区,我们都有充分了解本地法规特殊性的有经验的团队,”王瑞平强调。这种“本地化+全球化”的双重能力,正是浩思动力能够在多个国家市场实现落地的底气所在。王瑞平还进一步指出,供应链的本土化是出海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如果不去做本土化,那么在各种税收方面就不会有优势,在本地的竞争力可能也就体现不出来了。”
王瑞平对浩思动力出海战略的深度剖析,其实也是一次对中国汽车产业全球化进程的系统性观察。从技术路径到团队融合,从法规适应到供应链布局,王瑞平的讲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中国动力,全球赋能”的清晰图景。而这条路径,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零部件企业乃至整车企业出海的可复制范式。
更多内容详见视频和交流实录:
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
周晓莺:很高兴在IAA能够和您约到这次的交流。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您聊一下我们的出海模式。咱们现在走的是典型的技术出海,和传统意义上的贸易产品型出海,有何不同?
王瑞平:可以这么说,吉利动力实际上有很长的历史传承性,现在加上雷诺动力上百年的传承性,还有沃尔沃等,都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现在实际上结合起来了这些整体的优势之后,成立了Horse Powertrain浩思动力这家合资公司,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为我们增添了很多很强的能力,特别是全球化拓展的能力,这显然是有别于其他一些纯粹本土企业的地方,我们完全成为了国际化的企业。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大策略一定是走向全球的,要拓展全球市场。而且现在我们也是行业里的一个TOP级Tier 1,是一个能够供应动力总成系统解决方案的公司。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我们具备从产品到技术到整个研发体系全方位的全球化能力,这么做的好处,肯定比单一的卖产品,有更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其实这个逻辑有点类似于80年代的时候,中国开始引入全球产品的时候,早期的汽车工业,当时就是引进了很多世界顶级的主机厂到中国,来进行本地的投资落地,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技术滞后半拍引入进来的,先引入的产品,然后才逐步的有一些技术迭代进来。
我们今天的汽车工业出海,逻辑上有些类似,就是要走出去的市场,是我们的技术有优势的地方,是我们的产品有竞争力的地方,具备了这个条件,我们才可以走出去了。另一个方面,走出去如果只卖产品,相当于没有长期的、可持续的保护,或者说是不具备条件和基础。
我们卖的是动力总成产品,它实际上是和技术性很强的各个主机厂合作,与他们的整个整车战略规划,跟他们的整体产品的适配性关联非常紧密,因为我们是ToB(企业)的,不是ToC(消费者)的,所以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能把产品、技术加体系三位一体结合起来,一起去跟国外的企业建立长期的战略联盟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
而且基于现在的大环境,国外的实际形势,从五六年前,我们就开始做新能源转型。我们Horse 浩思的前身,在吉利动力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混合动力新能源技术,这些恰恰是现在新的浪潮,混合动力成为一种全球主导的技术路线,各个车企现在都很需要这样的一些技术,来匹配他们的整车产品和战略,所以我觉得恰恰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出海契机。
周晓莺:您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我们看这些年全球的电气化、智能化浪潮,中国市场发展的非常快,对于中国的供应链能力,尤其是电池、辅助驾驶系统等,大家的认可度都已经很高了,那么在传统的动力板块,您觉得现在中国在整个的动力品类里面,包括混动技术,在全球属于什么梯队?
王瑞平: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观念,过去在传统车型里面,大家认为动力总成是一个核心的技术专业模块,会认为这方面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相对来说不够领先,但实际上,在过去大概六、七年的时间里面,在新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在全球其他一些领先的主机厂All IN BEV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其实仍在持续的进行动力产品的迭代升级,特别是针对混动这种电气化动力总成,我们连续迭代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代产品。这五代的更新时间非常的快,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学习了很多,成长了很多。经历了这个过程,现在在动力尤其是混合动力体系里,我们在全球已经处于第一梯队了,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快”与“稳”的辩证法
周晓莺:现在国内的汽车技术架构平台迭代速度非常快,这种快速的迭代,其实跟传统的,比如像欧洲市场这种有严苛安全验证流程的市场,是不是会有一些冲突?
王瑞平:会有。我们的技术迭代很快,因为在中国,一个是市场发展很快,有需求产生了,我们必须快速的去产出新的产品。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市场竞争也比较厉害,卷的非常狠,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一定要快,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的快鱼吃慢鱼,武功唯快不破,一直都在讲这个快字。实现了快速迭代,在中国市场上就有机遇可以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这绝对是有非常大的优势。但是对于海外的市场,各个地区的法规要求不一样,出口到海外的产品,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现在欧洲在做欧七了,美国也有相应的法规要求,TIER3、TIER 4,而且在一些具体的验证,包括排放法规等很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跟中国也都是不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基础的部分我们是可以继续发挥我们快的优势,另外在本地法规的适应方面,我们现在有一个Horse浩思的国际化团队,无论在哪个地区,我们都有充分了解本地法规特殊性的有经验的团队,我们在这方面就形成了非常好的互补。所以,相关的本土法规适应性问题,可能是别人比较困难的地方,但对于我们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国内外团队双方很好的紧密契合起来之后,可以达到既可以发挥中国的快,然后又能够在海外不同国家和地区落地的效果。
周晓莺:走出了一条中西联合研发的新模式,对吗?
王瑞平:对的,可以这么说。
周晓莺:团队融合具体是怎么来做呢?比如说有没有区分主次?
王瑞平:团队融合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中国企业过去也有大量的国际化的公司,但是过去多数的领先技术,都来自于海外,那么这些年不一样的地方是,中国的企业的技术也开始走出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优势首先肯定是要遵从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人文需求,包括文化的差异化等。
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好呢?
首先我们有十几年的国际化合作经验,在2010年吉利并购沃尔沃之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十数年和沃尔沃合作的经验,我们长期在一起联合,特别是动力总程领域,我们联合开发动力总成,联合开发发动机,开发自动变速箱等,再到后来的混合动力,我们都是在联合的开展工作,所以我们双方整个的团队,文化的渗透其实已经非常成熟,大家互相也已经非常的了解。除此之外,我们还跟其他的海外顶级主机厂合作,可能有一些还受客户保密限制不能公开,但是总体来说,合作的都是欧美企业,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雷诺,也是股东之一。雷诺也用了我们的混合动力的动力总成,在韩国市场,在大科雷傲上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了当地的SUV领域的一个标杆车型。这些国际合作,其实都带给了我们很好的积淀,全球很多地区我们都合作过,所以这些不同的文化实际上我们的团队都在学习和成长。
总结下来就是以下几点,第一大家一定要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尊重对方的习俗;第二就是要去虚心的学习。我们去学习所有,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或者是给我们赋能,帮助我们成长。这些优秀的无论是技术还是理念,亦或是方法论,在十几年的过程中,多在帮助我们的团队快速成长,大家把这些都统一了之后,工作就会比较方便的开展了,大家都遵从国际的专业准则来做事,合作会非常的顺利;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结果,拿结果说话。从结果上面体现出来我们是务实的,我们是专业的,然后我们也是追求高效的,最终才会有很好的结果呈现,对团队产生了非常充分的信任。
所以实现国际化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大挑战的阶段。
周晓莺: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就借势修人,我们通过做每一个项目取得的成功,从小的积累锻炼的,实现团队全球化能力的整体提升。
王瑞平:是的,在实践的过程中实践出真知,其实就是在一个一个的国际合作项目中锻炼了团队,然后也实现了中西融合,大家能够互相理解,我们要理解欧洲思维,那么现在欧洲也在逐步的理解中国的速度,中国的一些理念。比如说,为什么中国能够这么快的做出来?这是他们经常问我们的一个问题,而且最后他们看到了非常好的结果。曾经一个欧洲的高管说过一句话,他们非常惊讶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么快又这么好的,还做出来这么多的产品。这是他们和我们合作多年之后,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那我们呢?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或者是我们给他们的回答就是,我们学习了很多,在与国际合作伙伴广泛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在虚心的学习所有.
就像之前咱们的一个传统的理念,三人行必有我师。中华传统的一种美德就是虚心学习,这也是外方比较接受我们的很重要的一方面。这个过程中大家就能够很快的和国际团队实现很好的融合,并用结果来表达我们团队的实力。
周晓莺:您刚刚提到其实咱们已经有了很多海外的顶级车企客户,您觉得他们对技术的要求,和对当地市场的适配性有什么差异吗?
王瑞平:有,其实这是另一个挑战。你这个问题也很好,我们做动力总成,实际针对不同的车型,要求差异很大。比如说对于豪华品牌,它对性能,对整体的品质、对一些特别细的细节要求都很高。当然还有在某些法规方面,像欧洲对安全的要求,就是安全功能,是欧洲很多年前就有的强制标准,但到中国实际上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跟欧洲车企的合作,我们把全套的相关技术全部都掌握了。再比如说在北美,其实也有它很多的特殊性,特别是对排放方面的一些要求非常苛刻,大家也听说过,此前有一些企业在这方面“翻船”过,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部分,就是不同地区法规的差异化。
从“中国优势”到“全球竞争力”
周晓莺:您提到的法规差异、文化差异,包括供应链,我想其实中国的完备性和海外也是不同的生态,您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在过程当中会碰到的挑战,让大家更加有具象的感觉。
王瑞平:你说的供应链很重要,我认为中国车企,或者是说汽车行业的相关企业,如果想出海,实际上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如果要做长远的发展规划,基于当前的大环境,实际上未来的发展趋势一定是要做本土化的,而这个本土化的,就要有本地的供应链支撑。
本地供应链,从目前我们考察的情况来看,每个地区虽然是不一样的,但是总体来说,特别是在新能源动力领域,毕竟这些年中国深耕该细分市场,所以发展比较快速,实际上在中国现在已经培养出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了。如果我们未来要走到全球其他市场的话,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希望这些供应链体系也能够跟随走出去,能够在不同区域形成本地化的系统化能力,整个生态环境、生态体系要建立起来,否则的话单独一个部件出海,是很难的,或者单独一个车企出去,也会很难,会遇到很大的挑战,整体成本是做不下来的。如果不去做本土化,那么各种关税、各种税收方面不会有优势,在本地的竞争力可能也就体现不出来了,如果做本土化,那么很显然供应链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周晓莺:它是很重要的支撑体系。
王瑞平:对,因为如果仅仅依靠海外各个地区他们自身的本地的供应链,要么在新能源领域,本地可能不那么擅长,还没跟上,要么成本就会非常高,就很难实现原来在国内的优势。
周晓莺:又快又好又便宜。
王瑞平:对,我们原来有一个口号,我们要做就做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质量、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最优的服务。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想要发展发挥中国企业的优势,还是要发挥我们过去积累下来的擅长的方面。
周晓莺:咱们在动力这个板块其实做出了最好的实践,给大家很好的参考。您觉得这种模式,是不是可以同样复制在供应链的其他生态里面?
王瑞平:会有。因为逻辑是相通的,道理是类似的,都是可以推广的。
周晓莺:其实这也是一种新模式,围绕我们技术上擅长的优势和创新,然后找一些新的模式出海,而不只是依循于传统的那几种方式。
王瑞平:对,而且我看到现在很多中国品牌企业,包括零部件企业,其实也已经在走出来,或者在走出来的路上,在海外很多地方建厂。
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些企业也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在过去十几年中,从他们起步然后到快速地跟随着中国的市场开始发展,然后一直到现在给很多外资企业都配套上了。给外资企业配套之后,他们的生产能力,也都扩展到了海外。
周晓莺:这感觉就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一样,他很自然的过了青春期就要开始独立了,不再只是在家里面,而是应该走向这个世界,去更大的舞台。
王瑞平:这也是一个人生的道理,其实逻辑都是类似的。
周晓莺:咱们现在在 IAA Mobility车展的现场,您应该也花了一些时间去逛了一下,今年有什么整体的感受吗?
王瑞平:IAA这边,按理说是欧洲主场,是整个汽车领域的一个技术的风向标,今年当然也不例外,也有很多企业,包括很多的零部件企业,都在参展和发布他们最新的技术。感受比较深的是,参展企业中,现在感觉海外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基本上已经平分秋色了,参展的规模和数量也是平分秋色了。主机厂我了解到的是欧洲企业有12家,中国企业有11家,基本上对半了,而且零部件企业也有很多中国企业来参展。
周晓莺:这应该也是我们的一种实力的象征,因为欧洲还是很讲求规则的,他们对产品的能力、技术的要求,原创性应该都是比较高的。
王瑞平:过去可能一二十年之前,我们的技术在起步阶段的时候,可能原创的能力还比较弱,但是通过最近十几年的快速学习成长,不断的产品迭代,大家其实已经具备了比较强的原创能力。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像我们Horse浩思,在混动领域有大量的技术创新,所以才能更好的满足不同市场,不同客户,包括高中低端的不同要求。既要满足高端要性能的需求,又要满足中低端在性能满足的情况下,可能更关注成本的需求。
我们产品的紧凑型要如何适配到各个不同的车型架构里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这个产品非常核心,它的匹配要求非常苛刻,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也要不断的进行创新,让它更加紧凑,更加具备成本优势。然后同时也要保障技术方面的领先性。
周晓莺:好的,谢谢王总。
联系邮箱:info@gasgoo.com
求职应聘:021-39197800-8035
简历投递:zhaopin@gasgoo.com
客服微信:gasgoo12 (豆豆)

新闻热线:021-39586122
商务合作:021-39586681
市场合作:021-39197800-8032
研究院项目咨询:021-39197921
